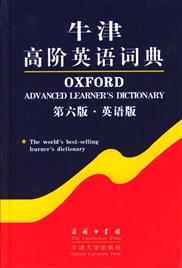显示全部序言
(一)
隙驷不留!对于我这般年龄的非英语国家(尤其像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英语教师来说,英人A.S.Hornby的名字可能是永远难忘的。个中缘由,容我由远及近道来。
我是1957年进的大学。由于中学连续六年“一边倒”学俄语,初入英文系从ABC学起,尤需合用的词典。当年人手一册的是老前辈郑易里先生根据英日辞书改编而成的《英华大词典》。我等的英文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这么一点水平,郑书功不可没。《英华大词典》内容赅通,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语各种用法的记录尤为详备,查得率高,其主要功能集中在receptive方面,亦即帮助读者求解释疑,而由于对productive功能兼顾不够,足观佳例无多,若要遣词造句作文而依靠郑书,那就难以得到多少帮助了。
这时,班上个别侨生和有海外关系的同学开始使用一本舶来品词典。借来一看,书题叫做Th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以下用中文简称《牛津高阶》),主要编者名叫A.S.Hornby,是位久在日本教授英语的专家。用过几次便发现,这部词典主要是替英语为非本族语的读者设计的,不但例证丰瞻,而且还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二语习得(虽说当时还不流行这种术语)的不少研究成果移植到了词典编纂中来,讲究“易简之理”,对动词用法模式、名词可数抑或不可数的特征、名词和形容词后随补足成分的各种常见搭配关系(如a decision to resign和be certain to need help)等分别以缩写字母或数码代号一一标岀,对指导production(学用)极有帮助。后来,不知足哪家出版社在大陆翻印了这郎词典,而词典的编者们似也以前瞻目光看到了巨大的中国市场,把一些大陆难以通过的政治色彩强烈的例证一一改去。如我记忆不谬,在down with这一短语之下原例为打倒某一政治派别,后被改为“无害的”“打倒语法学家!”。就这样,《牛津高阶》与郑易里的《英华大词典》如同锦桃对褓,一道成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学用英文的双拐!Hornby其人在英国文化委员会同侪口中昵称“灰公”(ash——A.S.H.的连写,鉴于他活到80,文坛尊宿,称之为公,当不算过),在我们同学中间也有雅号,叫做“红皮”,那是某位仁兄读他名字时发音不准,他人觉得滑稽,模仿着叫开了。《牛津高阶》就此成了“红皮”,回想起来,还颇有一点亲切的意味。
(二)
老蚌出新珠!时过半个多世纪,《牛津高阶》今天已出到第六版了,而当年拄着这根拐棍的我去年应邀参与了第六版英汉双解本的部分审订工作,对于这部迭经更新的词典何以始终深受欢迎的道理,似乎有了进一步的体认。
首先,《牛津高阶》把学习词典普遍采用的以简释繁的原则贯彻得十分出色,在第六版中把原来用于释义的3500词减至3000词,删削幅度达1/7。释义文字的削减符合我们中国人古话说的“辞尚体要,不惟好异”的道理;只求达意,不图妍巧,更是释文写作更高一层的境界。释义文字的削减还给非英语民族学生另一种启示,那就是学外语词汇量固然重要,但决非绝对的决定性因素。我常对学生说Edgar Allen Poe只用了3000多词就写出了诸如Annabel Lee这样的全部诗歌作品(小说用词自然不在此列),如今《牛津高阶》第六版削减释义文字似又进一步说明3000左右的词汇量,只要用得准确、娴熟,用出创意,表达还是大有可为的。
第二,与Hornby时代不同,今日的学习词典在淋漓尽致发挥production功能的同时,越来越注意加强reception的功能,各大出版社的竞争往往也把学习词典的收词量——特别是新词数量——视作重要方面之一。《牛津高阶》第六版一方面继承传统,注意教会学生活用,如在most条内以实例What did you enjoy (the) most?指明两可用法的同时强调非正式英语表达中通常省略the的事实,另一方面并不一味法故,而是根据语料库语言学最新的研究成果,遴选收录新词、新义4500条,以至收词总数多达八万,是为《牛津高阶》问世以来之最。不少新词新义完全利用语料库的积累,连1998年出版的大型《牛津英语词典》也未收录,如control freak,call centre,feel good factor,multi-skilling,stalking等。察视新词新义是件有趣的工作,如表示办公桌轮番使用而免空置的hot-desking一词已被包括《牛津高阶》的多种英语词典收录。近读外刊,说到南欧客籍工人去北欧或西欧打工,往往错开班头,以便两三人合租同一张床铺,减少费用,因称hot bed,似与hot desking有异曲同工之妙。试查《牛津高阶》hot bed未见此义,想来还是语料佐证不足之故吧。然而对一个词义衍生意识较强的学生来说,从此注意hot是否形成新的搭配表示轮番使用而免空置的意思,应该说是查词典的附带收获。
第三,今年,一名学生的学位论文写到辞书的美学问题——视觉美、工具美及其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习词典都采用“夹心彩页”以求满目奇胜。彩页包含何种内容反映编者的美学趣味和独特匠心。如以一组简图动人视觉,经由通感作用而刺激听觉(以挥鞭传crack声,碰杯传clink声,泡腾片溶于水传fizz声,等等),就是很有创意的做法。《牛津高阶》第六版除寻常衣食、游戏、动物、地图等插页外亦有佳思,那就是将实用美和观赏美相结合的16面“学习页”,从词的连接、搭配到如何撰写文电、履历以及如何构成新词,给读者具体而微的指导,批阅一遍,得益之多时辈未见其比。
不揣鄙陋,谨以上述两段文字祝贺《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六版)在中国大陆出版!
陆谷孙
复旦大学教授
2003年10月
隙驷不留!对于我这般年龄的非英语国家(尤其像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英语教师来说,英人A.S.Hornby的名字可能是永远难忘的。个中缘由,容我由远及近道来。
我是1957年进的大学。由于中学连续六年“一边倒”学俄语,初入英文系从ABC学起,尤需合用的词典。当年人手一册的是老前辈郑易里先生根据英日辞书改编而成的《英华大词典》。我等的英文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这么一点水平,郑书功不可没。《英华大词典》内容赅通,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语各种用法的记录尤为详备,查得率高,其主要功能集中在receptive方面,亦即帮助读者求解释疑,而由于对productive功能兼顾不够,足观佳例无多,若要遣词造句作文而依靠郑书,那就难以得到多少帮助了。
这时,班上个别侨生和有海外关系的同学开始使用一本舶来品词典。借来一看,书题叫做Th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以下用中文简称《牛津高阶》),主要编者名叫A.S.Hornby,是位久在日本教授英语的专家。用过几次便发现,这部词典主要是替英语为非本族语的读者设计的,不但例证丰瞻,而且还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二语习得(虽说当时还不流行这种术语)的不少研究成果移植到了词典编纂中来,讲究“易简之理”,对动词用法模式、名词可数抑或不可数的特征、名词和形容词后随补足成分的各种常见搭配关系(如a decision to resign和be certain to need help)等分别以缩写字母或数码代号一一标岀,对指导production(学用)极有帮助。后来,不知足哪家出版社在大陆翻印了这郎词典,而词典的编者们似也以前瞻目光看到了巨大的中国市场,把一些大陆难以通过的政治色彩强烈的例证一一改去。如我记忆不谬,在down with这一短语之下原例为打倒某一政治派别,后被改为“无害的”“打倒语法学家!”。就这样,《牛津高阶》与郑易里的《英华大词典》如同锦桃对褓,一道成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学用英文的双拐!Hornby其人在英国文化委员会同侪口中昵称“灰公”(ash——A.S.H.的连写,鉴于他活到80,文坛尊宿,称之为公,当不算过),在我们同学中间也有雅号,叫做“红皮”,那是某位仁兄读他名字时发音不准,他人觉得滑稽,模仿着叫开了。《牛津高阶》就此成了“红皮”,回想起来,还颇有一点亲切的意味。
(二)
老蚌出新珠!时过半个多世纪,《牛津高阶》今天已出到第六版了,而当年拄着这根拐棍的我去年应邀参与了第六版英汉双解本的部分审订工作,对于这部迭经更新的词典何以始终深受欢迎的道理,似乎有了进一步的体认。
首先,《牛津高阶》把学习词典普遍采用的以简释繁的原则贯彻得十分出色,在第六版中把原来用于释义的3500词减至3000词,删削幅度达1/7。释义文字的削减符合我们中国人古话说的“辞尚体要,不惟好异”的道理;只求达意,不图妍巧,更是释文写作更高一层的境界。释义文字的削减还给非英语民族学生另一种启示,那就是学外语词汇量固然重要,但决非绝对的决定性因素。我常对学生说Edgar Allen Poe只用了3000多词就写出了诸如Annabel Lee这样的全部诗歌作品(小说用词自然不在此列),如今《牛津高阶》第六版削减释义文字似又进一步说明3000左右的词汇量,只要用得准确、娴熟,用出创意,表达还是大有可为的。
第二,与Hornby时代不同,今日的学习词典在淋漓尽致发挥production功能的同时,越来越注意加强reception的功能,各大出版社的竞争往往也把学习词典的收词量——特别是新词数量——视作重要方面之一。《牛津高阶》第六版一方面继承传统,注意教会学生活用,如在most条内以实例What did you enjoy (the) most?指明两可用法的同时强调非正式英语表达中通常省略the的事实,另一方面并不一味法故,而是根据语料库语言学最新的研究成果,遴选收录新词、新义4500条,以至收词总数多达八万,是为《牛津高阶》问世以来之最。不少新词新义完全利用语料库的积累,连1998年出版的大型《牛津英语词典》也未收录,如control freak,call centre,feel good factor,multi-skilling,stalking等。察视新词新义是件有趣的工作,如表示办公桌轮番使用而免空置的hot-desking一词已被包括《牛津高阶》的多种英语词典收录。近读外刊,说到南欧客籍工人去北欧或西欧打工,往往错开班头,以便两三人合租同一张床铺,减少费用,因称hot bed,似与hot desking有异曲同工之妙。试查《牛津高阶》hot bed未见此义,想来还是语料佐证不足之故吧。然而对一个词义衍生意识较强的学生来说,从此注意hot是否形成新的搭配表示轮番使用而免空置的意思,应该说是查词典的附带收获。
第三,今年,一名学生的学位论文写到辞书的美学问题——视觉美、工具美及其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习词典都采用“夹心彩页”以求满目奇胜。彩页包含何种内容反映编者的美学趣味和独特匠心。如以一组简图动人视觉,经由通感作用而刺激听觉(以挥鞭传crack声,碰杯传clink声,泡腾片溶于水传fizz声,等等),就是很有创意的做法。《牛津高阶》第六版除寻常衣食、游戏、动物、地图等插页外亦有佳思,那就是将实用美和观赏美相结合的16面“学习页”,从词的连接、搭配到如何撰写文电、履历以及如何构成新词,给读者具体而微的指导,批阅一遍,得益之多时辈未见其比。
不揣鄙陋,谨以上述两段文字祝贺《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六版)在中国大陆出版!
陆谷孙
复旦大学教授
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