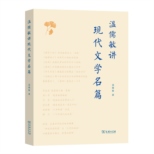关联图书
-
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78.00
如何让文学名著走进公众的生活——从《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看“讲说体”与经典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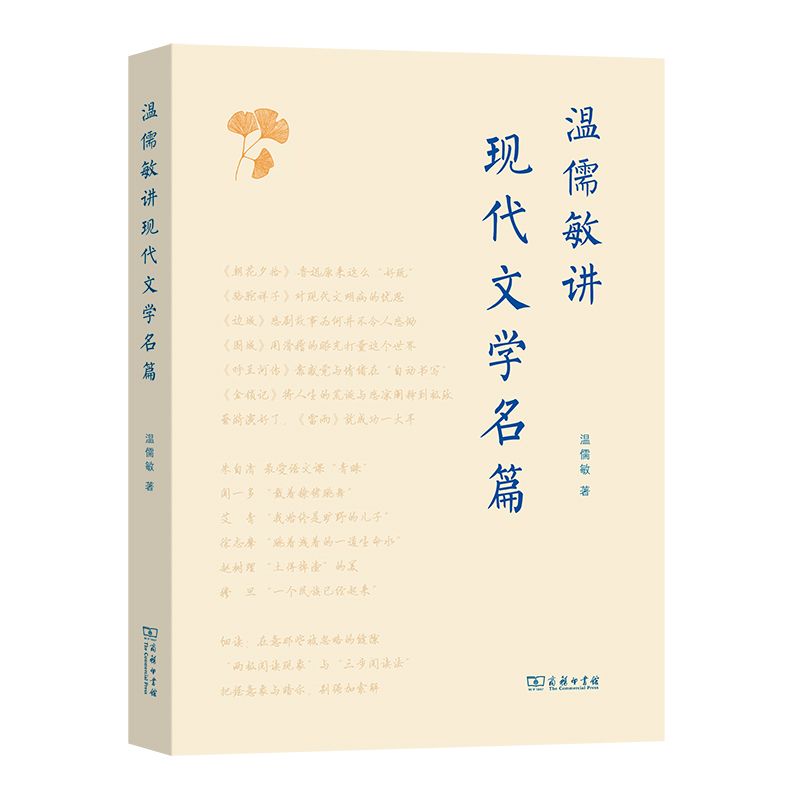
《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近读《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商务印书馆2022年9月第一版),颇感兴趣。该书如何从复杂而争议甚多的现代文学史中选取名篇,特别是用何种方式、语言和腔调来讲授名篇,可以说别具一格,我称之为“讲说体”。
在与温儒敏先生交谈中听他说过,多年前他主持过一套“名家通识讲座”(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俗称“十五讲书系”,涉及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诸多领域,所邀请的作者大都是各个学科领域权威,用类似讲座的方式介绍相关学科的“通识”,迄今已经出版五六十种。据温儒敏说,当初主持这套书,想落脚在“名家”和“通识”这两个特色上,但不容易。很多“名家”没有功夫或者不屑于写这类读物,而有些“名家”答应写了,却仍然专业性太强,如同写教科书,难于深入浅出。“十五讲”原打算出版100种,20多年过去了,也只完成原计划的一半,也就因为有实力的能进能出的作者难于物色。
我能体会温儒敏的苦心,也有过尝试“讲说体”的类似的经历。多年前,我应邀为山西希望出版社主编一套未成年人精神成长丛书,对标的是1930年代朱自清先生和他的一些同仁编写的开明文库系列,但能够胜任的名家都很忙,而有些名家所写的文体文风却又不太符合年轻人阅读。由是,这套书出了第一套后,就无以为继。
其实,“讲说体”并不少见,只是学术性和普及性都能很好兼顾的比较少罢了。前些年很“火”的“百家讲坛”之类,讲求的是将史事故事化,力求通俗而有趣,甚至有很多离学术较远的“戏说”和发挥,能赚得收视率或流量,也大致可以归入“讲说体”,其面向的观众多是平民。而温儒敏所提倡的“讲说体”主要是名作鉴赏,转化学术研究的成果,面对的是有一定人文学养的读者,目的仍然在于经典的阐释与普及。
据温儒敏说,“讲现代文学名篇”这本书,是在他多年在北大讲授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基础上整理的。讲稿带有课堂讲授的口气与师生互动的氛围,自然有“讲说体”特别的风格。我替《名作欣赏》向温儒敏约稿,想请他从自己的代表作——比如《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等——专著中选择一部,我们再组织评讲。温儒敏说自己没有什么代表作或“经典”,还不如选新出的这本名篇讲析。温儒敏为何如此重视这本鉴赏类普及性的读物?他认为,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新传统”(现对于古典文学),事实上已经弥漫于当代国人的文学生活之中,其影响不可低估。而他讲授现代文学,就试图把这些见惯不惯的“新传统”影响加以梳理沉淀,把优秀的作家作品经典化。他的拟想读者是大学生、中学语文老师,需要深入浅出,而且侧重鉴赏,示范文学鉴赏阅读的“方法性知识”,把专业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普通读者也能接受的通识。这样的鉴赏,是对经典的彰显,更是结合现实开掘经典,让经典走向生活,为广大普通读者接受。
温儒敏这本书的重要启示,或者我更看重的是,就是如何让文学名著走进公众的生活。在我看来,文学鉴赏舍我无它。在当今学术生产体制中,看重的是“论文”,鉴赏性的“讲说体”文章容易被认为不够“规范”,是进入不了研究成果的“层级”的。但文学研究怎么能离开对于文学审美鉴赏与批评这个基础呢?好的文学鉴赏文章,是作者将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文学史知识、对时代性特征及对所面对的读者的深刻理解,化为了自身生命的血肉,然后去拥抱同样用生命血肉创作出来的文学名著,并因此走进了血肉之躯的读者的生活与生命,让读者能从一棵树的形状,窥探到森林的风貌;从一瓢海水,品味到海水的苦涩。这样的对文学本位的深度回归,这样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功力,这样的将绚烂归于平淡的历程,非有理论家的素养、文学史家的视野、世事洞明的眼光,不可得之。而对如此鉴赏能力的提倡,却也正是对今日科技吞噬人文导致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的无人之血肉人之体温的技术化弊端的及时的有力矫治。
人文科学,其本质在作用于人。古代中国,一向视诗词为“文”之正宗。但明清之际,伴随着社会转型中市民阶层的兴起,曾经作为主流的诗词辉煌不再,作为不入流的“小道”的小说蓬勃于民间。而梁启超不为既有偏见所束缚,不失历史时机地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于是,有了鲁迅的弃医从文,有了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正宗之位。还是鲁迅,当五四新小说不能有力地介入社会生活时,宁愿为文坛中人讥嘲而花数年之功,弃小说而让杂文由无名而成为著名的“匕首”与“投枪”。还有坚守着从古代到五四民间价值谱系的赵树理,也是宁入“文摊”不入“文坛”却因此而成为了一代乡土中国之子。如是观之,当今日中国在经受着从未有过的“历史大变局”之际,当各种此起彼伏争辩不休的人文理论因此不能以理念对之给以有效解读之时,将以文学名著作为人之历史经验的载体并以今日生命感性对之给以直接感应并因此给各种理念以再阐释空间的文学鉴赏,将文学鉴赏从“形似”的知识论,回归并彰显到其“神”所原有的方法论价值论,焉知不会祛除原有对其的偏见而一领时代之风骚?那或许是别一格式的现代启蒙,亦是深得今日全民阅读之真谛之魂魄。
还应该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所采用的文体形式,我称之为“讲说体”,是用口语体进行对名著的讲授与鉴赏的。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与其时的对现代语体文的倡导,双潮合一,构成了对国人情感与语言表达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但在这之前,更不应该忽视的是黄遵宪提出的“我手写我口”。“手”与“口”的统一是显性的变革而为国人所瞩目,但更内在更为根本的,是“我”的提出,这实在是可以视为是五四“人的文学”因此而来的“拓人荒”的拓新,对几千年“吃人”历史反思与控诉的时代性先声。这“人”,众所周知,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因之,给了“我”以合法性的存在。“讲说体”则是“我手写我口”的现代性继承。不仅仅是表达方法表达形式,更是表达主体“我”的存在,并因此构成了对当今时代技术、资本、时尚“复制”而形成的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批判与对抗。文学鉴赏中的“趣味无争辩”“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则给这一对“我”的守护,披上了可行性的漂亮外衣,也使文学鉴赏成为了批判与对抗“复制”这一时代弊端的排头兵。
“讲说体”的“讲说”,是为了“听”,“听”是“讲说”的对象化实现,也因此构成了对“讲说”的限制。温儒敏的这本书预设的“听者”是大学生、中学语文教师及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因此,过于专业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创新性观点,虽然作者对之亦颇有研究,但也大都点到即止,引而不发,不作过多的涉猎。这是对“听者”的尊重,也是“讲说者”的自觉。
当然,对“听者”的尊重,不是对“听者”的迁就,而是在“听者”的基础上,有所拓宽与纵深,有继续思考的空间与新的生长点的引诱。这在这本书中,可谓比比皆是,兹不一一。需要强调的则是,这其中有着如温儒敏所说的“方法性知识”,其实,这“方法性”所抵达的,实是“价值性”的深处,那就是“讲说者”与“听者”之间的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现代主体间性关系”,这在“我”作为“个体”终于在当今中国“浮出历史地表”并在新的一代国人中渐成汹涌之势时,尤具现实意义。这对“无我”的各种场合各种身份的“发言”与“讲说”,尤具警示意义。这也是力图使语言成为存在的“家园”而非“牢狱”的切实努力。
行文至此,我想,我们或许可以把这样的文学鉴赏,视为学术经典之一种:即对文学经典作经典性的鉴赏与解说,换句话说,就是让这样的鉴赏与解说,本身也具有着经典性。我知道,已经有许多论者,强调了温儒敏的老师王瑶先生的老师朱自清先生曾经有过《经典常谈》《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等鉴赏类的经典之作,并认为温儒敏所继承的是他的“祖师爷”(温儒敏的导师是王瑶先生,而王瑶是朱自清先生指导的研究生)这一文脉的。近还看到,温儒敏专门为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所写的导读(收人民文学出版社《经典常谈》单行本),其中亦强调阅读经典的一般“方法性知识”,行文口气仍然使用“讲说体”,大概也是一种文脉传承吧。
以对文学经典作经典性鉴赏的方式,把学界的研究成果有效地化为中国公众面对人文困惑的精神资源,让学术经典走出各种“壁障”走进公众生活,从而实际地实现着人文研究的价值,是实现这“人间情怀”“岗位意识”并达到“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的践行方式之一,而温儒敏的这本《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就是这践行的一个成功个例。
(原载于《 中华读书报 》2025年03月19日18 版,作者系山西太原师范大学教授)
- 寻找改变饮食生活的根源2024-11-22
- 打造巨兽:战争与税收如何催生现代欧洲? 2024-09-23
- 普及训诂知识 传承中华文化2024-09-05
- 《现代小说化读》: 拆解文学经典创作要诀2024-08-22
- 胜地都游遍 吟诗倾肺肝——回忆翰老的有关诗及其他2024-08-07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